
在更高的天空下:写给分歧中的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从一场公共分歧引发的秩序、信仰与弟兄之爱的思考
作者:赵晓
引言:分歧之中,是否仍有共同仰望的天空?
在当下的公共讨论中,分歧往往并不止于分歧本身。它们常常迅速滑向阵营化与标签化,判断被简化为态度,人被推着站到非此即彼的位置上。久而久之,我们甚至难以分辨:自己究竟是在讨论公共问题,还是在为某种情绪与归属感而战?
最近,张雪忠教授和郭于华教授之间一场围绕美国政治人物的公共分歧,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不小的回响。争论的表面,是是否支持某一位政治人物;但真正引发张力的,显然并不只是这位政治人物。这场分歧更像一面镜子,照出了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日益显化、却长期未被认真梳理的深层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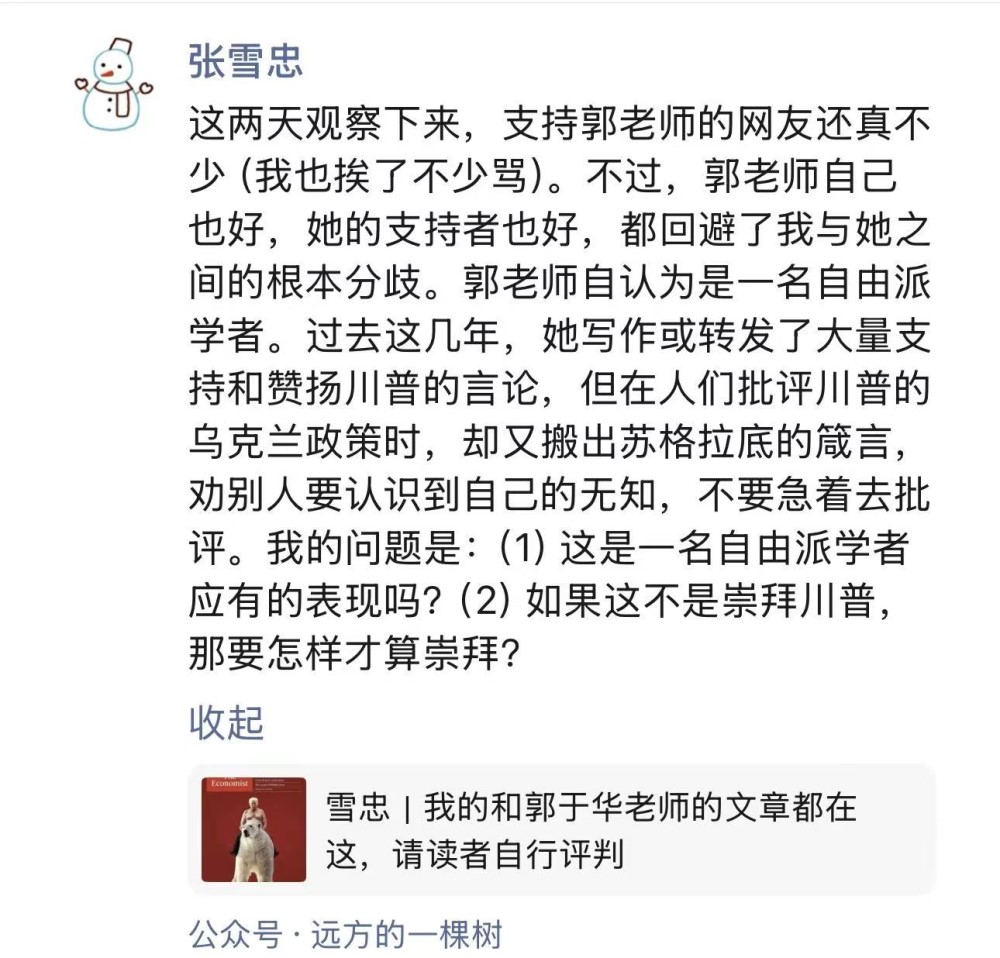
需要首先澄清的是:分歧本身并不是问题,甚至强调分歧也完全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分歧被敌我化。
在任何一个健康的公共空间中,分歧都是常态。真正值得警惕的,不是意见不同,而是当分歧不再被视为可以讨论的差异,而被理解为价值上的敌对、道德上的高下,甚至人格上的可疑。那时,公共讨论便不再是增进彼此理解的努力,而开始演变为彼此否定的交锋。
正因如此,本文并不试图裁决谁在争论中“更正确”,也无意对任何具体立场作出道德评判。本文更关心的,是一个更基础、也更长远的问题:当我们在政治判断、制度偏好乃至文明走向上出现重大分歧时,是否仍然可能在某个更高的维度上,承认彼此的诚实,尊重彼此的良知,并继续把对方视为同路人?
换言之,在分歧之上,是否仍有一片可以共同仰望的真正自由与真理的天空?

一、制度锚定与信仰锚定:分歧从何而来?
如果我们暂时把情绪与立场放在一边,冷静地回看围绕美国政治反复出现的公共分歧,会发现一个值得认真对待的事实:分歧的真正来源,并不在于谁是否理性,也不在于谁更珍视自由,而在于人们各自把“秩序的最终锚点”安放在了哪里。
对中国自由派而言,“制度锚定”是不言而喻的,制度始终是最可信、也最可操作的依托。权力必须被限制,政府必须被约束,个人权利必须通过成文规则得到保障。这一整套逻辑,构成了自由主义最坚实的思想内核。因此,当某位政治人物表现出对程序的轻视、对制度的冲撞,甚至在言行中显露出强烈的个人意志色彩时,自由派产生警惕乃至反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并非情绪反应,而是源自其一贯的学理立场与深刻的历史记忆。
然而,另一种判断路径同样真实存在。对许多保守主义者来说,制度固然重要,但它并不是秩序的起点,而更像是秩序的结果。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本身的正当性来自何处?是谁在制度之上限制制度的滥用?

正是在这里,“信仰锚定”的视角开始显现其意义。
以美国为例,这个国家之所以在现代政治史上显得特殊,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一部成文宪法,而是因为它在建国之初,就明确拒绝将权力的最终来源安放在人间的任何有限之物之中。
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宣告:
“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独立宣言》由此确立的根本原则是:
权利不是国家“赋予”的,而是政治“承认”的
民族、国家、政府、多数意志,都不是权力的终极授权者
政治共同体的任务,是保护一种先于政治而存在的权利秩序
在这一前提下,美国政治秩序从一开始就完成了一次根本性的“去神化”:
国家不是神
制度不是神
多数也不是神
它们都必须被置于一个终极的上位秩序之下,接受超越政治本身的道德审视与约束。
这一点极其关键,包含着一个很多政治学教材都没有说透的重大事实:美式宪政最基本、最深层的权力制衡,并不发生在制度之中,而首先发生在“权力是否被承认为终极”这一层面。
三权分立→权力之间的横向制衡
去神化→权力与终极正当性之间的纵向制衡
后者,比前者更根本。
也因此,当美式宪政的信仰根基逐渐被淡化,甚至被否认时,分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人们对同一位政治人物作出截然不同的判断,也就不再只是立场差异,而是源于对美国宪政秩序根基的不同理解。自由派更多关注程序是否受损,保守主义者则更在意价值是否失锚。当锚点不同,彼此的理性并没有消失,而是必然导向不同的判断路径——一种侧重程序与制度的理性,另一种侧重价值与终极秩序的理性,并最终呈现为结构性的分化。说到底,理性并不是悬浮的,它总是被锚定在某种“最终所指”之中。

二、当上位秩序消失,分歧为何走向敌我?
在一个健康、有序的公共讨论中,分歧本身并不可怕。真正令人不安的,是分歧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从问题之争,转化为人格与动机之争;从“你怎么看(What do you think?)”,变成“你是谁(Who are you?)”。
但少有人注意到,这一变化,往往发生在一个关键前提被抽空之后:当社会不再承认存在高于各方之上的共同秩序时,分歧便会在心理与道德层面被重新编码为敌我关系。事实上,当缺乏上位秩序作为共同参照,人便几乎不可避免地转而借助身份与道德,对彼此作出裁决。
在美国传统的新教文明语境中,即便政治立场发生分化,人们仍然默认存在一个超越政治的上位秩序——under God(在上帝之下)。正是在这一前提下,政治对手仍被视为同处于这一上位秩序之下的共同体成员,如同一个家庭中的“弟兄”,是需要被尊重、被说服、被制衡,却不应该、不可以被消灭的对象。
然而,一旦这一上位秩序退场,裁决权便不可避免地回到“下位”的人手中——回到多数、权力、话语优势,或当下最具动员力的道德叙事之中。分歧因此不再只是判断不同,而会被迅速道德化、身份化,并最终走向敌我化。
当对方不再只是“错了”,而被视为“不义的”“危险的”,公共讨论便不再以说服为目标,而转向压制与排除。这种滑坡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阵营,而是秩序真空之下的普遍风险。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极端反对基督教制度与教会历史的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却仍然对耶稣本人保持敬意,才显得格外耐人寻味。这一张力提醒我们一个常被忽略、却至关重要的区分:基督教作为历史制度,基督徒作为不完全的人,与耶稣本人,并不能被简单等同。
正是由于这一区分的成立,即便在是否接受基督教信仰的问题上立场迥异,人们仍可能在对耶稣人格与教导的敬重中,保留一种更高层次的道德共识,并由此避免将分歧彻底推向敌我对立。
也因此,即便对宗教制度持强烈批判立场,人们仍然可以在终极信仰与道德维度上彼此对话;而当这一界线被抹平,一切被压缩为立场正误,公共空间便会迅速失去弹性。
也正是在这一观察视角下,我注意到张雪忠教授对耶稣所表达的敬意,也注意到他所批评的郭于华教授同样对耶稣怀有敬意。至少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未站在彼此的对立面,而是同处于一片关乎自由、真理与良知的更高天空之下。正因如此,我仍然看见中国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在那片更高天空下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的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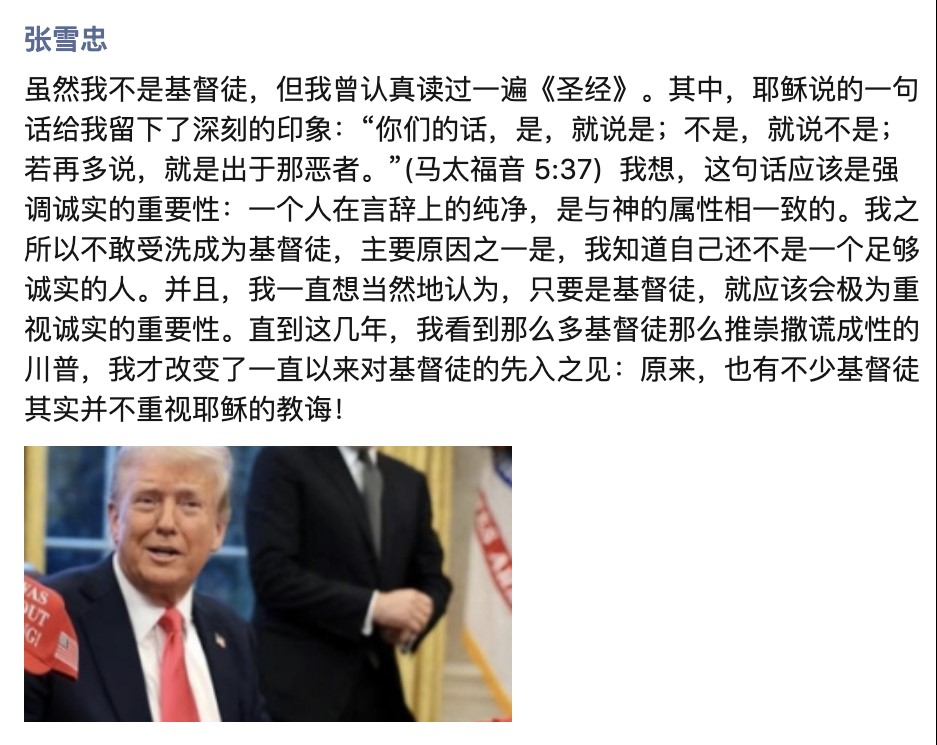
三、底线共识:在分歧中如何仍然彼此相待为弟兄?
既然分歧并不会迅速消失,一个现实问题便摆在面前:是否存在某种可能,使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即便在重大判断上持续分歧,仍不至于走向彼此否定?
一个可行的起点,并不是追求全面一致,而是重新确认底线共识。
第一,承认对方的诚实与良知。分歧中最具破坏性的,并非判断不同,而是对动机的道德化推断。一旦默认“与你不同,必然意味着不诚实”,对话便已终止。
第二,拒绝将制度或立场神圣化。自由派需要警惕制度被绝对化,保守主义者同样需要警惕传统被神圣化。双方在这一点上,其实拥有共同的敌人——把有限之物抬升为绝对之物的冲动。
第三,保留对上位秩序的敬畏感。无论这种敬畏被理解为信仰、道德律,还是超越个人意志的责任结构,它都意味着:人并非终极裁判者。
在这一意义上,许多中国自由派学者并非对信仰与超越毫无兴趣。相反,不少人始终保有强烈的终极关怀与道德理想。他们或许对宗教制度和组织保持距离,却对耶稣基督的言行与教导怀有真诚的敬意。被称为“天国宪法”的登山宝训,其核心并非权力原则,而是人格秩序——谦卑、怜悯、清心、饥渴慕义,以及对和平的执着。
正是在这里,自由派与保守主义者之间,或许存在一个常被低估的交汇点:对终极秩序、人格秩序高于权力秩序的共同直觉。

结语|在更高的天空下
写到这里,我已无法继续保持抽象的旁观姿态。因为这场讨论,不只是关于他人的分歧,也贯穿了我自身的思想路径。
我曾长期站在自由主义传统之内,对制度理性心怀敬意。正是这一传统,教会我尊重规则、警惕权力、珍惜良知的独立性。对此,我始终心怀感激。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我也逐渐意识到:仅靠制度理性,并不足以承载文明的全部重量。制度可以限制权力,却难以回答权力为何必须被限制;制度可以规范行为,却难以生成终极的约束与盼望。正是在这样的反思中,我的思想逐渐向保守主义靠拢。
但我也愈发清楚地看到:思想上的转向,并不自动意味着人格上的成熟。而保守主义也不仅意味着一种立场或政见,更意味着人格与风范。在克制、谦卑与耐心上,我常常发现自己远不如一些自由派学者。他们或许在终极信仰上尚未迈出“惊险跳跃”的一步,却在做人上始终守住分寸,在分歧中仍愿意保留尊重与善意。这不仅让我自省,也让我格外珍惜与他们之间那种真实而不功利的友谊。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与自由派并非陌生人。相当多的保守主义者,正是从自由主义传统中走来。只是当他们意识到,那片天空不足以承载终极问题时,才开始抬头,寻找更高的参照。这并非对自由主义的放弃,而是一种延伸——对“秩序究竟安放在哪里”的继续追问,也是对“何谓真自由、以及如何捍卫并保障自由”的进一步思考。
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自然浮现:当自由主义的天空不再足够宽广,我们是否一定要彼此分道扬镳?抑或,是否可能在更终极的天空之下,重新彼此承认为弟兄?
这并不是一个策略性问题,而是一种深切而严肃的盼望。因为如果在分歧中,我们连彼此相待为“人”的能力都失去了,那么无论制度多么精巧,文明本身都已开始流血。
我所盼望的,是另一种前景:在分歧仍然存在的前提下,中国的自由派与保守派依然能够彼此尊重、求同存异;不仅为公共秩序争论,也为人格秩序守望;在那更高的天空之下,不急于彼此定罪,而愿意彼此等待。
在两千多年的基督教传统中,那片天空有一个清晰而温柔的名字——耶稣基督。他并不站在“足够好”的那一边,而是站在所有承认自身不完全、却不愿放弃真理的人中间。也正是在那片天空之下,分歧不必走向敌我,判断不必升级为审判,人仍然可以在不同路径之后,彼此珍惜。
或许,这正是中国公共文明在漫长转型之中,仍然值得珍惜的一点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