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剧《白色巨塔》谈起
作者:歌珊
在忙碌的秋冬季学习和工作之后,寒假开始了,于是在一个放松的午后,点开2003年版日剧《白色巨塔》。这部片常被认为是日本电视剧史上最具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的作品之一,编剧、导演、演员、配乐等,现在欣赏仍然值得高评分。现在很少看剧,因为时间成本需要衡量。
重温这部片,加上近期深受赵晓老师两次带队日本游学的丰盛属灵大餐所启发,令我思考基督信仰与日本现代文化的关系。白色的巨塔使我联想到巴别塔,片尾曲《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东教授女儿常佩戴十字架项链……剧中不乏基督信仰的元素。该剧的创作团队里,查不到任何关于基督信仰的背景。刘军宁老师曾提出一个极佳观点:世界是个圣经现象。因此,看任何事物,愿从《圣经》角度来试做解读。

一、一座“白色”的人性高塔
《白色巨塔》改编自山崎丰子的同名小说,山崎丰子不是基督徒作家,但她写出了“没有上帝的世界,人如何彼此吞噬”的真实图景。
剧中“白色巨塔”指的是:
医学殿堂
权威、理性、科学
社会精英构建的制度与等级
剧的片头用了一个白色的巨塔,但这座塔并不“圣洁”,而是由权力、野心、虚荣、妥协与沉默一层层堆砌而成,是没有上帝的并不纯洁的世界。
剧情核心冲突不是医术高低,而是:人在没有上帝、没有终极审判的体系中,会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努力”“正确”和“专业”,走向目标。

二、“白色巨塔”与“巴别塔”:极其深刻的对应
《白色巨塔》不是关于医学的剧,而是关于“人能否自救”的寓言。把它联想到巴别塔,或许这并不是牵强,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主题性”的理解,因为人类不在上帝之下就在法老之下、在自我之中。
在这座塔中,人们以知识为阶梯,以头衔为荣耀,以成功为义,他们相信,只要足够聪明、足够努力、足够被承认,就能站在他们自己的医学领域之巅。然而,这座塔越高,人心越孤独。财前五郎的一生,像极了巴别塔的建造者——他并非愚昧,也并非无能,而是确信自己理当依靠才能和手段得到最高的位置和名利。
1、巴别塔的本质
《创世纪》第11章4节:“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问题不在“建造”,而在:
为自己立名
人取代上帝
用理性与技术抵挡审判
财前的问题也在于此,不在于“医学”上的建造,而是在于成就、名利的野心。

2、白色巨塔正是现代版巴别塔
在剧中:
医学成了“终极权威”
教授头衔、论文、学会 = 荣誉的凭证
病人逐渐变成“案例”“数据”“阶梯”
而财前五郎就像巴别塔式人物的化身,他才华横溢、意志坚定、不信任何“超越性的存在”,坚信自我的努力——“我值得登顶”。他的悲剧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他登顶了也无法救赎自己。
三、片尾曲《Amazing Grace》:不是装饰,而是审判
《Amazing Grace》这首诗歌的核心不是安慰,而是悔改: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白色巨塔》里的大多数人:
专业上看得很清楚
灵魂上却完全失明

因此,整部影片形成了强烈反讽:
画面:白色、理性、冷静、权威,就如整个日本社会的色调。
音乐:罪人、迷失、恩典、拯救,就如上帝等待迷失灵魂回家。
我在欣赏日本的文学、影视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发自内心的问题:即便随处可见基督元素,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走近、了解,更不用谈接受这个恩典,而仅仅是把它当作无关己事的存在。
四、人物的信仰象征与“无声的神学”
1、东教授女儿的十字架是偶然,还是一个极为克制却意味深长的设定?
它是个记号,象征的是不在权力结构中的“他者”,不争、不斗、不发声,却始终带着“审判与怜悯的记号”。
东教授的女儿像个天真纯净的旁观者。十字架在这里不是宗教宣告,而是:一个始终在场、却无人直视的存在。

正如日本二战后的文明转型里,如今现行的制度体制,是由麦克阿瑟将基督信仰所产生的文明制度植入的。基督是始终在场的,确是被无视的。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近,充斥着各类“神明”却无视真正掌权的真神。
就像剧中的“良知”:一直在那里,但大多数人选择绕开。
在日本,若你跟人传福音,很可能被告知:这被视为“不礼貌”的,你应该克制。严格遵守各种约定俗成的界限,是应该的,礼貌地将人捆绑。
2、里见修二:不是“完美义人”,而是受限的良心
很多人把里见看作“正义化身”,但从信仰角度看,他更像:未被拯救,却是践行朴素真理的人;他有坚持,却常常孤独;他有底线,却没有改变制度;他没有登上高位,不以权利“胜利”为目的。
他有的是受限的良心,因为他也未曾被救赎,他是在没有救主的世界中,艰难行走的义人。这反而让故事更真实,也更残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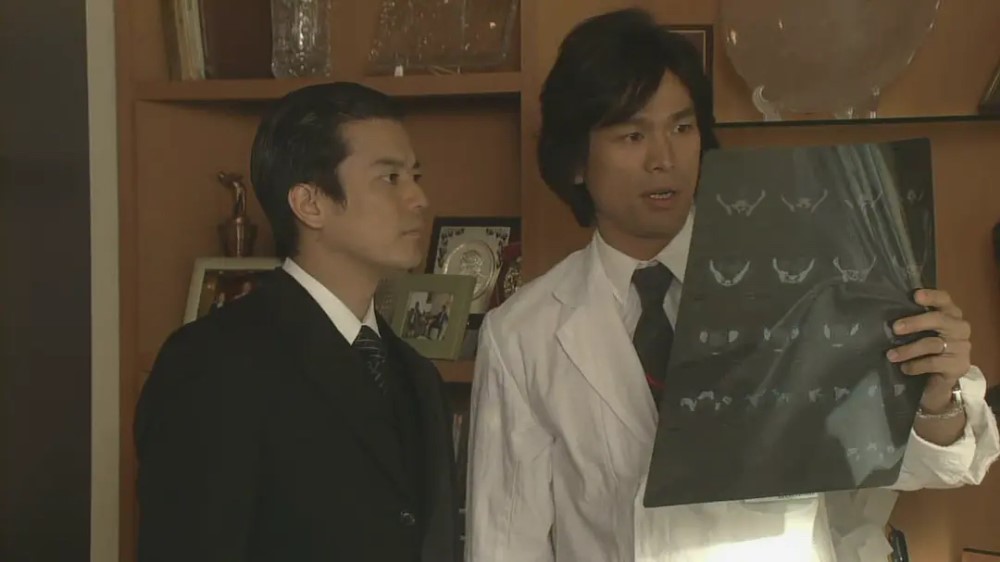
五、剧中人物对照圣经人物
1、财前对比扫罗
《申命记》第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
《白色巨塔》中最震撼的,是财前与里见,两位医生并不是“善恶对立”,而是两种“看似都合理的人生道路”。

财前五郎就像扫罗式的人物,“被拣选,大有恩赐,却被自己吞噬”。扫罗与财前都具备被众人认可的才能、制度内的一定权柄,初期并非纯粹的恶。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转折点:他们开始把“上帝的心意”替换成“自己的判断”。
扫罗的问题不是失败,而是“不肯顺服”。《撒母耳记上》第15章:扫罗保留亚玛力王和牲畜,自以为“有道理”。他仍然献祭、仍然敬虔,但上帝说:“听命胜于献祭”。

财前也是如此:他救过人,他懂医学,他甚至在某些时刻“并不想害人”。但当“真相”妨碍他的登塔之路时,他选择:让良知为事业让路。
《罗马书》第1章22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财前的结局犹如扫罗,扫罗的王位仍在,人却已经空了;而财前教授在手,生命却正在流失。生命逻辑的结果,你很难说这不是在上帝的法则里。

而里见似乎是个义人的象征。里见选择了另一条路,他没有赢得掌声,也没有改变制度,只是在每一次可以妥协的时候,选择不妥协。可在一个没有救赎叙事的世界里,义人只能孤独。
里见是个良心有限的人——因为只有上帝是全知全善者,他是个假设在“上帝沉默”的世界里,义人又会走多远的对比例子。
2、“法利赛人”群像
整部剧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其实不是财前,而是——那些“没有恶意”的共犯者,他们正对应《圣经》中的法利赛人:守规则、重程序、轻生命、害怕失序多过害怕不义。
耶稣对法利赛人最严厉的指控是:“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
而白色巨塔里:没有人直接杀人,但每一次签字,都是一次“合法的放弃”。没有一个人有“绝对正义”。

六、整部剧的终极问题——信仰问题
《白色巨塔》最终不是在问:谁对谁错?谁升谁降?
而是在问三个更深的问题:
1、如果人没有终极审判,正义靠什么站立?
2、如果成功就是“被承认”,那失败者是否连尊严都不配?
3、如果医学能救身体,却不能救灵魂,人到底被医治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白色巨塔》几乎是一部让人强烈意识到“人不能自救”的剧,
没有出现上帝,却处处显出“缺席的上帝”的作品。

七、疑问:为什么日本影视中常出现“隐秘的基督符号”
在信主之后,我常常愿意用“神学式的阅读”来看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当然包括曾经喜欢的文学、艺术、影视等等。
日本人有敬畏心,日本不是完全的“无神论社会”,而是“失去超越的社会”。神道重秩序、轻救赎;佛教重修行、回避“此岸”;只有基督教提供“审判—恩典—拯救”的完整叙事。

日本创作者往往不接受基督教义,却无法忽视“缺席的上帝”。于是他们使用十字架、圣诗、教堂、殉道意象作为一种对“终极意义”的借用。基督符号在日本常被当作“良知的语言”。
我非常喜欢今敏的《东京教父》,也是如此情况,创作者并无基督信仰背景,却创作了一部“平安夜寓言”式的电影:里面没有圣徒,只有罪人;没有讲道,只有怜悯;没有奇迹的解释,却不断发生“恩典式的偶然”。它似乎在说,“如果上帝真的降临在东京的街头,祂最可能被谁遇见?”答案显然不是成功者、正常者、体面者,而是社会边缘人、被遗忘的人。但它不宣告任何信仰,只是一部讲述“恩典”残影的电影。有机会再说。

在《白色巨塔》中,十字架不是宣教,《奇异恩典》不是赞美,而是:一种“你本该知道,却选择不看的东西”。
这正是日本作品的悲剧美学。日本文化极擅长描写:努力却失败、正直却孤独、清醒却无解。而基督信仰恰恰提供了他们感知到,却不敢宣告的答案。这类作品本来就在向“信仰的方向敞开”,只是它停在信仰的门口,不肯向前再迈步。
当片尾响起《奇异恩典》时,它带有安慰或审判的意味:“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我曾眼瞎,如今得看见……”只是,在这部剧中,被寻回的可能性,留给了会思考信仰问题的观众自己。

《白色巨塔》提醒我们:若人拒绝仰望上帝,那么再洁白的塔,也终将成为人的坟墓。
上帝啊:
当我们建造白色巨塔,求你阻止我们以成功代替顺服;
当我们只讲局部真理,求你光照我们不愿面对的全貌;
当你沉默,求你赐我们仍然信靠的心;
当我们渴望审判他人,求你让我们铭记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离了你,人不能自救。阿们!





从日剧《白色巨塔》谈起
从日剧《白色巨塔》谈起
作者:歌珊
在忙碌的秋冬季学习和工作之后,寒假开始了,于是在一个放松的午后,点开2003年版日剧《白色巨塔》。这部片常被认为是日本电视剧史上最具思想深度和现实意义的作品之一,编剧、导演、演员、配乐等,现在欣赏仍然值得高评分。现在很少看剧,因为时间成本需要衡量。
重温这部片,加上近期深受赵晓老师两次带队日本游学的丰盛属灵大餐所启发,令我思考基督信仰与日本现代文化的关系。白色的巨塔使我联想到巴别塔,片尾曲《奇异恩典》(Amazing Grace),东教授女儿常佩戴十字架项链……剧中不乏基督信仰的元素。该剧的创作团队里,查不到任何关于基督信仰的背景。刘军宁老师曾提出一个极佳观点:世界是个圣经现象。因此,看任何事物,愿从《圣经》角度来试做解读。
一、一座“白色”的人性高塔
《白色巨塔》改编自山崎丰子的同名小说,山崎丰子不是基督徒作家,但她写出了“没有上帝的世界,人如何彼此吞噬”的真实图景。
剧中“白色巨塔”指的是:
医学殿堂
权威、理性、科学
社会精英构建的制度与等级
剧的片头用了一个白色的巨塔,但这座塔并不“圣洁”,而是由权力、野心、虚荣、妥协与沉默一层层堆砌而成,是没有上帝的并不纯洁的世界。
剧情核心冲突不是医术高低,而是:人在没有上帝、没有终极审判的体系中,会如何使用自己手中的“努力”“正确”和“专业”,走向目标。
二、“白色巨塔”与“巴别塔”:极其深刻的对应
《白色巨塔》不是关于医学的剧,而是关于“人能否自救”的寓言。把它联想到巴别塔,或许这并不是牵强,而是一个非常准确的“主题性”的理解,因为人类不在上帝之下就在法老之下、在自我之中。
在这座塔中,人们以知识为阶梯,以头衔为荣耀,以成功为义,他们相信,只要足够聪明、足够努力、足够被承认,就能站在他们自己的医学领域之巅。然而,这座塔越高,人心越孤独。财前五郎的一生,像极了巴别塔的建造者——他并非愚昧,也并非无能,而是确信自己理当依靠才能和手段得到最高的位置和名利。
1、巴别塔的本质
《创世纪》第11章4节:“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
问题不在“建造”,而在:
为自己立名
人取代上帝
用理性与技术抵挡审判
财前的问题也在于此,不在于“医学”上的建造,而是在于成就、名利的野心。
2、白色巨塔正是现代版巴别塔
在剧中:
医学成了“终极权威”
教授头衔、论文、学会 = 荣誉的凭证
病人逐渐变成“案例”“数据”“阶梯”
而财前五郎就像巴别塔式人物的化身,他才华横溢、意志坚定、不信任何“超越性的存在”,坚信自我的努力——“我值得登顶”。他的悲剧不是人生失败,而是:他登顶了也无法救赎自己。
三、片尾曲《Amazing Grace》:不是装饰,而是审判
《Amazing Grace》这首诗歌的核心不是安慰,而是悔改: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am found;Was blind, but now I see.
《白色巨塔》里的大多数人:
专业上看得很清楚
灵魂上却完全失明
因此,整部影片形成了强烈反讽:
画面:白色、理性、冷静、权威,就如整个日本社会的色调。
音乐:罪人、迷失、恩典、拯救,就如上帝等待迷失灵魂回家。
我在欣赏日本的文学、影视的时候,总是有一个发自内心的问题:即便随处可见基督元素,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走近、了解,更不用谈接受这个恩典,而仅仅是把它当作无关己事的存在。
四、人物的信仰象征与“无声的神学”
1、东教授女儿的十字架是偶然,还是一个极为克制却意味深长的设定?
它是个记号,象征的是不在权力结构中的“他者”,不争、不斗、不发声,却始终带着“审判与怜悯的记号”。
东教授的女儿像个天真纯净的旁观者。十字架在这里不是宗教宣告,而是:一个始终在场、却无人直视的存在。
正如日本二战后的文明转型里,如今现行的制度体制,是由麦克阿瑟将基督信仰所产生的文明制度植入的。基督是始终在场的,确是被无视的。
日本文化与中国文化相近,充斥着各类“神明”却无视真正掌权的真神。
就像剧中的“良知”:一直在那里,但大多数人选择绕开。
在日本,若你跟人传福音,很可能被告知:这被视为“不礼貌”的,你应该克制。严格遵守各种约定俗成的界限,是应该的,礼貌地将人捆绑。
2、里见修二:不是“完美义人”,而是受限的良心
很多人把里见看作“正义化身”,但从信仰角度看,他更像:未被拯救,却是践行朴素真理的人;他有坚持,却常常孤独;他有底线,却没有改变制度;他没有登上高位,不以权利“胜利”为目的。
他有的是受限的良心,因为他也未曾被救赎,他是在没有救主的世界中,艰难行走的义人。这反而让故事更真实,也更残酷。
五、剧中人物对照圣经人物
1、财前对比扫罗
《申命记》第30章19节:“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
《白色巨塔》中最震撼的,是财前与里见,两位医生并不是“善恶对立”,而是两种“看似都合理的人生道路”。
财前五郎就像扫罗式的人物,“被拣选,大有恩赐,却被自己吞噬”。扫罗与财前都具备被众人认可的才能、制度内的一定权柄,初期并非纯粹的恶。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转折点:他们开始把“上帝的心意”替换成“自己的判断”。
扫罗的问题不是失败,而是“不肯顺服”。《撒母耳记上》第15章:扫罗保留亚玛力王和牲畜,自以为“有道理”。他仍然献祭、仍然敬虔,但上帝说:“听命胜于献祭”。
财前也是如此:他救过人,他懂医学,他甚至在某些时刻“并不想害人”。但当“真相”妨碍他的登塔之路时,他选择:让良知为事业让路。
《罗马书》第1章22节:“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
财前的结局犹如扫罗,扫罗的王位仍在,人却已经空了;而财前教授在手,生命却正在流失。生命逻辑的结果,你很难说这不是在上帝的法则里。
而里见似乎是个义人的象征。里见选择了另一条路,他没有赢得掌声,也没有改变制度,只是在每一次可以妥协的时候,选择不妥协。可在一个没有救赎叙事的世界里,义人只能孤独。
里见是个良心有限的人——因为只有上帝是全知全善者,他是个假设在“上帝沉默”的世界里,义人又会走多远的对比例子。
2、“法利赛人”群像
整部剧中最令人不寒而栗的,其实不是财前,而是——那些“没有恶意”的共犯者,他们正对应《圣经》中的法利赛人:守规则、重程序、轻生命、害怕失序多过害怕不义。
耶稣对法利赛人最严厉的指控是:“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 ——《马太福音》第23章23节
而白色巨塔里:没有人直接杀人,但每一次签字,都是一次“合法的放弃”。没有一个人有“绝对正义”。
六、整部剧的终极问题——信仰问题
《白色巨塔》最终不是在问:谁对谁错?谁升谁降?
而是在问三个更深的问题:
1、如果人没有终极审判,正义靠什么站立?
2、如果成功就是“被承认”,那失败者是否连尊严都不配?
3、如果医学能救身体,却不能救灵魂,人到底被医治了什么?
从这个角度看,《白色巨塔》几乎是一部让人强烈意识到“人不能自救”的剧,
没有出现上帝,却处处显出“缺席的上帝”的作品。
七、疑问:为什么日本影视中常出现“隐秘的基督符号”
在信主之后,我常常愿意用“神学式的阅读”来看这个世界的所有事情,当然包括曾经喜欢的文学、艺术、影视等等。
日本人有敬畏心,日本不是完全的“无神论社会”,而是“失去超越的社会”。神道重秩序、轻救赎;佛教重修行、回避“此岸”;只有基督教提供“审判—恩典—拯救”的完整叙事。
日本创作者往往不接受基督教义,却无法忽视“缺席的上帝”。于是他们使用十字架、圣诗、教堂、殉道意象作为一种对“终极意义”的借用。基督符号在日本常被当作“良知的语言”。
我非常喜欢今敏的《东京教父》,也是如此情况,创作者并无基督信仰背景,却创作了一部“平安夜寓言”式的电影:里面没有圣徒,只有罪人;没有讲道,只有怜悯;没有奇迹的解释,却不断发生“恩典式的偶然”。它似乎在说,“如果上帝真的降临在东京的街头,祂最可能被谁遇见?”答案显然不是成功者、正常者、体面者,而是社会边缘人、被遗忘的人。但它不宣告任何信仰,只是一部讲述“恩典”残影的电影。有机会再说。
在《白色巨塔》中,十字架不是宣教,《奇异恩典》不是赞美,而是:一种“你本该知道,却选择不看的东西”。
这正是日本作品的悲剧美学。日本文化极擅长描写:努力却失败、正直却孤独、清醒却无解。而基督信仰恰恰提供了他们感知到,却不敢宣告的答案。这类作品本来就在向“信仰的方向敞开”,只是它停在信仰的门口,不肯向前再迈步。
当片尾响起《奇异恩典》时,它带有安慰或审判的意味:“我曾失丧,如今被寻回;我曾眼瞎,如今得看见……”只是,在这部剧中,被寻回的可能性,留给了会思考信仰问题的观众自己。
《白色巨塔》提醒我们:若人拒绝仰望上帝,那么再洁白的塔,也终将成为人的坟墓。
上帝啊:
当我们建造白色巨塔,求你阻止我们以成功代替顺服;
当我们只讲局部真理,求你光照我们不愿面对的全貌;
当你沉默,求你赐我们仍然信靠的心;
当我们渴望审判他人,求你让我们铭记你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离了你,人不能自救。阿们!
2026-01-01
Date :
2026-01-01
最新文章
赵晓:“最后的咒诅书”,还是沉默前爱的呼唤?
启蒙系列之十二——回得去吗?给走完理性与后现代之路的人——在启蒙之后,重新理解信仰、恩典与文明的希望
王志勇:真正的大使命
“启蒙系列”之十一——理性的坍塌:尼采、后现代与启蒙的思想终局——当启蒙开始怀疑自己
“启蒙系列”之十——当历史成为神:理性如何完成自己的极权形态?——启蒙逻辑在思想史中的现代极端形态
“启蒙系列”之九——启蒙的多重结局:不同文明结构下的现代性变体——一种启蒙类型学的比较框架
雪薇:香港火灾与神的律法必要成全
周斌:三个唯独
热点文章
启蒙系列之十二——回得去吗?给走完理性与后现代之路的人——在启蒙之后,重新理解信仰、恩典与文明的希望
周斌:三个唯独
“启蒙系列”之九——启蒙的多重结局:不同文明结构下的现代性变体——一种启蒙类型学的比较框架
王志勇:真正的大使命
雪薇:香港火灾与神的律法必要成全
“启蒙系列”之十——当历史成为神:理性如何完成自己的极权形态?——启蒙逻辑在思想史中的现代极端形态
“启蒙系列”之十一——理性的坍塌:尼采、后现代与启蒙的思想终局——当启蒙开始怀疑自己
赵晓:“最后的咒诅书”,还是沉默前爱的呼唤?
每日灵修汇编20260119-20260125
相关文章
文章分类
联系我们
因时间精力有限,电子邮件无法保证每封都回复,但我们会认真阅读每封邮件,推荐微信联系,谢谢理解!